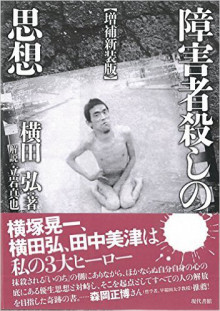橘逾淮為枳,由餃子從中國東傳的故事或許可以說得更清楚,透過飲食,看餃子如何在文化間穿梭,餃子從中國傳到日本的故事,可以看到文化的接觸、交融、轉換,再加以傳播的過程。
餃子對於日本人而言,現在已經是相當普及的國民料理,和拉麵一樣,深入民間、隨手可得,並且每個地方的餃子都會有點不同。我們先到日本最多餃子店的城市宇都宮看看,這裡有一座維納斯的餃子雕像。
維納斯的餃子雕像
宇都宮在日本關東的北部,從東京往東北地方的大城,也是栃木縣的縣治,這裡是日本最多餃子店的地方,光是宇都宮市,就有上百家的餃子店,還有一尊知名的餃子維納斯像。從宇都宮車站的西出口,在人行天橋的下面有一尊以維納斯為造型,但維納斯卻被餃子所包覆的石像,這尊石像相當出名,宇都宮的人都知道,為什麼要刻畫一座餃子的的雕像呢?
因為餃子是宇都宮人自豪的鄉土料理。其實不只宇都宮,在日本全國各地,餃子堪稱是現代的國民美食,但如果追溯餃子的流行時間卻相當晚,主要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,還與日本侵華、滿州國的成立有關,我們先從餃子在日本最早的紀錄看起吧!
江戶時代的餃子紀錄
雖然餃子在江戶時代並不普及,但已經留下一些紀錄,當時很多與中國有關的事物,都跟著名的儒學者朱舜水扯得上邊,這位日本有名的儒學者其實是明朝遺民,因為不想降清,將中國的很多文化帶到日本。在《朱舜水談綺》這本書中提到將鴨肉的餃子獻上給水戸藩的藩主德川光圀(後來大家稱他為「水戸黄門」),據說是水戸光圀日本第一個吃到餃子的(他也是第一個吃到拉麵的)。爲什麼是鴨肉呢?因為當時的日本人不吃四腳的動物,所以餃子常用的豬肉就變成鴨肉了。
除了朱舜水以外,要了解日本和中國的關係,也得到長崎,曾經任職長崎奉行的中川忠英,在《清俗紀聞》這本書中提到從浙江商人那邊理解到清國人吃餃子,是一種很像燒賣的東西,由於燒賣較早傳到日本,所以日本人必須要用燒賣理解餃子。
江戶時代幾本關於異國料理的書籍,像是《卓子式》、《新編異國料理》和《普茶料理仕樣》都有餃子的紀錄,當時餃子的作法和現代差不多,就是用薄薄的麵皮加入肉餡,再包起來,但在當時的各種紀錄中提到的都是用蒸籠蒸,而不是放在滾燙的水中煮。
或許是當時傳入日本的飲食習慣都是南方廣東系的料理,點心類習慣用蒸的,所以水餃在江戶時代的紀錄,大部分是用蒸的。但不管是甚麼作法,餃子在江戶時代沒有很多日本人吃過是可以確定的。時代往下,我們看看明治維新時候的日本人喜不喜歡吃餃子。
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餃子
明治維新對於日本人而言不只是船堅炮利上的革新而已,也不只是西方政治、思想和文明的引進,還包含了飲食的革命,這時開始吃四隻腳的動物,是以前所不吃的,或是不能公開吃的,而餃子最主要都是包豬肉,所以相較於明治維新以前,有較多的人知道餃子。
如果要了解餃子在日本的普及,我們該如何著手找史料呢?或許可以從兩方面思考,一個是當時餐廳的開設,思考餃子餐廳鎖定的族群是誰?其二就是從料理書當中追尋。前者我們可以從電話簿、介紹美食的書、旅遊雜誌開始。或許也可以從一些報紙的文章,美食作家的評論開始找起,我們先看看當時日本中華料理的流行狀況。
吉田誠一的書《美味且便宜的中國料理哪裡找?》提到1920年代東京的中國料理店大量增加,總共有兩千多家。然而,餃子店的相關材料很少,因為大部分的中華料理都是賣廣東、上海菜系,沒有北方人常吃的水餃,只有南方的蒸餃。
我們來看看二次戰前的料理書和食譜好了,相較於餐廳,這是平常主婦在家中烹飪的菜色,看看其中是否有餃子的蹤跡。從草野美保的研究中,她從「味の素食文化センター」和國會圖書館中整理出所有中華料理關係的書籍、雜誌,在總數730種的書中,有餃子的只有五十種,時間從明治20年(1887)一直到二次大戰。
此一時期的料理書中可以看到對於餃子的認識較多,不只是蒸餃子、還有水餃子、煎餃子的作法,在料理書中都有介紹。但日本人此時還是不大認識餃子的,雖然從料理書上看到餃子,但這時的料理書不像我們現在的圖文並茂,有些還有精美的圖片,讓人一看就懂,並且按圖索驥,當時的料理書要讓日本人了解甚麼是餃子,必須從他們所理解的料理中介紹。所以這時的料理書說餃子像「柏餅」和「豚饅頭」。
甚麼是「柏餅」?薄薄的外皮,裡面包著甜蜜的紅豆餡,端午節時中國人吃棕子,日本人吃柏餅。日本的關西人還有吃粽子的習慣,但關東人吃柏餅是江戶時代中期才發展起來的習俗,柏餅可以分為紅豆餡和味噌餡,為了區分兩者,會將葉子反過來包。因為怕一般人不知道餃子是甚麼,所以此一時期的料理書透過日本的甜點「柏餅」加以介紹。
有趣的是,放在水中煮的水餃,當時的日本人稱為「中國北方的燒賣」(北支の燒賣)。日本人還是將餃子與燒賣視為同一種東西,是點心的一種,而不像中國北方將水餃視為主食。
二次戰前的餃子雖然在日本已經有些書籍介紹,但還未大量流行成為國民美食,按照學者田中靜一的研究,餃子會在日本盛行是因為日本侵華的關係,大量的日本人進入中國戰場,而且主要的地點在滿州、華北。除了軍事人員外,眷屬和相關的人員也到中國居住,當時北方的飲食習慣,像是麵食、包子或是餃子都成為日本人較為熟悉的食物。
下集當中我們就看看餃子如何成為日本的國民美食,一個地方級的城市宇都宮就有一百多間餃子館。除此之外,日本的餃子不僅在國內風行,也走向世界,成為世界認識日本料理的一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