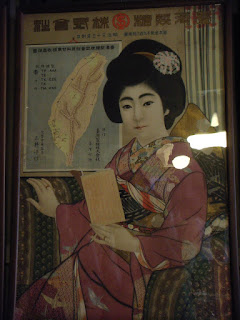「我想下地獄,看看那些迫害我們的人在地獄受著什麼樣的苦。」
「當時我很害怕看到吉普車來,怕蔣經國找他去談話,然後就再也回不來了。」
「直到現在,一講到國民黨,我仍然痛苦萬分,情緒激動。」
夏君璐女士在接受楊照的訪問時,語帶哽咽的說。夏君璐女士是殷海光先生的遺孀,臺大出版社在最近出了這一本既新且舊的書《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》,說舊是因為最早的一封信始於一九四六年夏君璐寫給殷海光,一開始說「寫這封信的原因,完全在於我彷彿應該寫信給你」,當時夏君璐只有十七歲;說它是一本新書則是這些書信是殷海光先生從未出版過的文字。
夏君璐女士目前已經八十三歲了,講起六十多年前的那場相遇,帶著嬌羞的說當初是她追求殷海光的,當他因緣際會的住進夏家時,年輕的夏君璐在日記當中說著和殷海光出遊的那個日子,記著「這是個永生難忘的一天」。從一九四六年開始,殷海光和夏君璐開始通信,夏君璐當時還在高中就讀,殷海光在中日戰爭之後服務於國民黨的機關報《中央日報》,並且擔任總主筆,兩人的信中所言大部分都是思念之情,所呈現出來的殷海光和哲學家與批評家的殷海光完全不同,哲學家的殷海光是講邏輯,重論理,批評時政的殷海光是勇敢的對抗、批判蔣介石政權,連桀敖不馴的李敖都說殷海光是「蛟龍式」的人物,《書信錄》當中的殷海光則是柔情似水、感情豐富的人,《書信錄》當中寫著:「也許,妳此時正在熟睡吧!睡的多麼美好!假如我能變作一隻小鳥,我要冒這寒風和冷雨,振翅從這窗子飛出,飛過長江,飛過高山,飛到妳身旁,溫暖溫暖我自己呀!」多麼《未央歌》的文字阿!

除此之外,我們還可以看到大時代在信中所留下的痕跡,一九四八年之後,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,節節敗退,夏君璐從南京到湘潭、廣州,然後一人獨自搭船到基隆,「其實我們戀愛的經歷,痛苦多於快樂,擔心受嚇多於享受,並且不時陷入患得患失的情緒中,眼淚更不知流了多少。我們愛情的小舟在時代的大海中顛頗翻騰,竟能平安的駛入基隆港,實在不可思議。」
歷經千山萬水而到台灣的夏君璐,開始在台大就讀,當時殷海光於哲學系任教,兩人尚未婚嫁,仍繼續頻繁的魚雁往返,直至一九五三年結婚後才停止通信,此時也是殷海光開始參與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的編輯,1950年代,《自由中國》是當時蔣介石高壓威權統治下唯一能夠公開發行的不同聲音,殷海光身為雜誌的主筆,強調自由、民主和科學,批判時政,組織反對黨,他的貢獻就如同李敖所說的:「在使人頭腦清楚方面,做到了中國有史以來沒人做得到的大成績。他以簡明的分析、高明的遠見、清明的文筆,為歷來糊塗的中國人指點了迷津。」然而,蔣氏流亡政權不需要高明的遠見,不需要有人指點迷津,他們就是要成為流亡的皇帝,1960年9月,《自由中國》遭到查禁,負責人雷震入獄,殷海光被迫離開「自由」思想的臺大,不到數年即得胃癌抑鬱而終。殷海光自述自己是五四後期的人物,「這樣的人物,正像許多後期的人物一樣,沒有機會享受到五四人物的聲華,但卻有份遭受著寂寞、淒涼和橫逆。」

在2011年的夏天,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本書,這不是殷海光先生那些強調自由主義思想、批判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文字,也不是那些重邏輯、富有哲思的著作,從這本書可以看到一個動亂大時代下知識份子的愛情、生活與家庭,也可以理解他的抱負與理想。
多年來,一直有人鼓勵夏君璐出版一本回憶錄,然而她寫寫停停,始終無法完成,她自謙不擅於書寫,但從下面的文字來看,就知道她是過於謙虛了:「三個星期來月光第一次灑在我的床上,我曾氣憤了很久,搬到這寢室躺在床上再不能看見天空的晶星,月亮幾乎是圓滿的,是金黃色的。比往日更幽美更聖潔了。我身上蓋的被褥是我自己洗自己縫上的。一種寧靜的隱密的喜悅投到我心胸。」可以知道殷夫人是個感性的人,她或許無法以太過分析而理性的文字回憶過往那個沉重的時代;或許是她不習慣說自己,因為她是個以殷先生為中心的順服妻子;或許殷先生的背影太巨大,不管怎樣寫都覺得不完整;或許是傷痛太沉重,無法以文字描述她的遭遇。
出版《書信錄》的過程,有如電影一般精彩,在整理房子的過程,滿滿一盒的信紙,母女的討論下,彷彿電影的情節重現於現實之中,女兒透過將信一個字一個字的打下來,瞭解父親在公領域之外的情感;殷夫人在重讀這些信的過程當中,回憶也重新鮮活了起來。

李敖在〈我的殷海光〉說:「如今,《自由中國》和殷海光都成了歷史名詞,看到二十年來群眾還是那麼混蛋,我必須說,殷海光的啟蒙工作的成果是悲劇性的,因為真正受到他影響而能繼續發揚光大的工作,並沒展開,《自由中國》所帶來的那些開明與進步,好像又混蛋回去了。一九七六年冬天我第一次坐牢出獄,我最強的一個感覺就是:『混蛋比以前多了!』混蛋多,就反證了殷鑑已遠,所以我說,殷海光的光芒是悲劇性的。」
混蛋現在還是很多,像被李敖稱之為陰蝨般的蔣氏政權餘孽,不過,值得高興的是,現在殷海光這樣悲劇性的人沒有了,沒有了表示我們的政治權力不再因為人民的抵抗而產生悲劇,當殷海光這個名字已經成為遙遠的記憶,當殷夫人所經歷的痛苦可以透過述說、記錄和回憶加以批判,在歷史的長河中,已經彰顯臺灣社會的巨大變化。